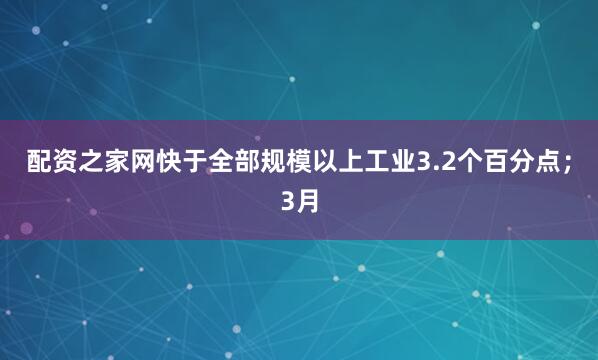翻开著名作家张新科最近出版的长篇巨著《铁语》,硝烟的气息扑面而来。作为一位身历战争洗礼的老兵,我抚摸书页的手似有些颤抖——书中那些跨越国界的抵抗身影、血肉铸成的生死情谊,瞬间勾起了曾经的记忆。虽说场景与人物不同,但透过文字读到的是人间的大爱与真诚。这部历时八年淬炼而成的50多万字鸿篇,不仅填补了中韩联合抗战文学的叙事空白,更在历史褶皱中打捞起被时光遗忘的英雄魂魄。为正义、为民族、为信仰奉献青春和生命的英雄,再度使我热血沸腾。
双重突围:历史深描与文学重构
张新科以近乎考古学的严谨对待创作:四赴韩国踏访义士纪念馆,沿韩国义士的足迹遍访十三城,在上海石库门、嘉兴的烟雨楼、长沙深巷大院、重庆的防空洞等地捕捉历史的残记。这种“战地侦察兵式”的历史调查,赋予了作品“钢浇铁铸的质感”。当读到中国船娘在嘉兴南湖上冒险掩护韩国义士的情节,我眼前浮现的是当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时用竹篓背运弹药的壮族姑娘——战争中的平民英雄,永远是民族脊梁最生动的体现。
展开剩余72%《铁语》采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准则。在恢宏历史框架中注入文学的蓝图。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凡组建“铁血团”的史实,与中国青年崔立骏等人物的命运交织,恰如我们连队当年真实战报与炊事班老兵的口头传奇的交融:“历史与文学的双螺旋结构”,让抗战烟火的温情,令我有亲临现场之感。
暗夜微光:普通人的英雄主义叙事
张新科的笔锋最令人感动人处,在于“无名者的深情凝视”。书中那位默默守护抗日情报站的药房老板,让我想起当年连队里因误触地雷而牺牲的通讯员小黄——他们从未出现在战史名录上,却是战争齿轮连续传动时不可或缺的螺钉。作者刻意把笔头对准车夫、船娘、职员、学生等平民群体,通过这些平凡的人传递“亲仁善邻、厚德载物”的中华传统伦理。这种“去英雄化的英雄叙事”,恰如弹片伤痕:表面微小,内里却蓄满生命的壮烈。当崔立骏为保护金凡扑向敌人时,我仿佛听见了自己当年在谅山高地冲锋时的嘶吼。“战争美学的精髓”,从来不是将领的立功奖章,而是普通战士把自己的血肉之躯铸成最后一颗子弹的瞬间。
创作密码:钢与血的叙事美学
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代表作家,张新科既学习过理工,也学习过文科,还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多年,对中外文化耳熟能详,属于典型的“跨界”作家,“出圈”大家。因此,他的作品展现出“工程思维与文学激情的奇妙融合”。著名评论家汪政主席精准喻其为“文学芯片”——在精密如军用地图的情节设计中,埋伏着引爆情感的重磅炸药。嘉兴、南京、长沙、重庆等地防范日谍的惊险场景,紧张度堪比我们当年穿越雷区:每次落脚,步步惊心。
最震撼人心的是对抵抗意志的淬火书写。金凡在嘉兴南湖船上宣言:“铁会生锈,但铁语不朽”,恰如我们当年阵地上“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的血书。张新科用“铁语”作题,实则吟诵着一曲“钢铁与血肉的二重奏”——前者是武器,后者是使用武器的人。前者终将锈蚀,而后者却能以精神形态永垂不朽。
强权必败:跨国情谊的当代镜鉴
中国原驻韩大使邱国洪称《铁语》为“中韩友好的文化纽带”时,我想起当年战友坚持人道主义,用急救包救治异国战俘的情景。“战争中的跨国善意”,是人性对兽性的终极反抗。战争中的情形是未曾经历战争的人难以理解的。对与错,是与非,源于道义,止于真诚。《铁语》再现中国百姓掩护韩国志士的“侠义精神”,本质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证言。在当年的战地教育时,我也曾听指导员讲述老一辈援越抗美的故事。战场上的跨国情谊,比和平时期的盟约更为炽热。
张新科以八年光阴精雕细琢打磨这部作品,恰似兵工厂精心打磨一柄利剑。书中那些中韩志士制造的水壶炸弹,与我们在猫耳洞共享的云南竹筒饭,构成了跨越时空的战争交响曲。当金凡与崔立骏相逢和分手之际同举杯品茗之时,我又嗅到了一九七九年春节时阵地上那瓶茅台的芬芳——所有反侵略战争中的情谊,都源自同样的勇气与悲悯。
暮色中的书页翻动声,仿佛当年展开作战地图的沙沙作响。张新科用十三座城市的地气与四赴韩国的风尘,熔铸出这部“钢水沸腾般的作品”(范小青主席的评语)。当金凡先生在结尾处望着黄浦江再次响起“铁会生锈,但铁语不朽”时,我抚摸着桌上的纪念章,豁然彻悟:所有值得书写的战争,最终都是为了守护生命本身的尊严。
作为另一场战争的参与者,与创伤的承载者,我在《铁语》的跨国叙事中,辨认出所有反侵略战争的精神公约数——那就是在血火中淬炼的人类情谊,比任何武器更易击穿时间的铁幕。
发布于:江苏省炒股配资官网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国家允许的配资平台2023如今它既是球鞋收藏家的必入款
- 下一篇:没有了